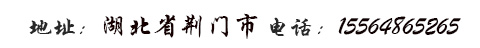谢春卉彩虹衣裳
|
补骨脂素价格大概是多少 https://m-mip.39.net/baidianfeng/mipso_4325343.html风语 穿上道布尔吉用9张羊皮缝制的袍子我立刻变得举步维艰,这件衣服的质量和它的保暖系数成正比,道布尔吉的妻子道力玛怕我们冷执意要我们穿上这些皮袍。 这片草原上只有道布尔吉一家,站在他家院子里向四周望去,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他家南面是一片冰封的湿地,湿地里高大的芦苇从远处看我以为是森林,东面有三所空置的房子,这些房子是风的住所,草原上的风一年四季不停地刮,有些风偷懒或者刮到这里刮不动了就跑到这些房子里躲起来。 我站在院子里的时候一轮红日正破晓而出。这片土地上的太阳只为道布尔吉一家东升西落,坐在他家屋里一边喝着奶茶就可以目睹整个日出日落的过程,但是起先我并不知道。五彩的霞光将天边和雪原次第晕染,我像个朝圣者一样站在一望无际的雪原上恭迎一枚太阳的降临。风在耳边发出轰隆隆的巨响。这些风一边奔跑一边大喊,风使这么大劲喊什么呢? 头天晚上道力玛来我们毡包问,明天去四方山你们去吗?我说去。据说四方山有位老人能听懂风语。我问道力玛,我们可以去拜访他吗?道力玛莞尔一笑说能。道力玛的声音平静、柔和充满了女性魅力,无论我提出什么要求道力玛都说好、可以、行,但她说“能”的时候莫名其妙拉着长声,好像有揶揄的味道。 我们出发的时候太阳刚好升上天空。道力玛为我们的爬犁铺上毡子,道布尔吉和他们十一岁的大女儿分别骑上了两匹骆驼,道力玛怀抱两岁半的小女儿坐上了另一架爬犁,我们的两架骆驼爬犁就出发了。 太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好像这些影子正随时准备跑掉。风从西面刮过来,风扬起雪,到处都是雪雾。我问过道力玛,四方山在哪儿呢?道力玛说就在前面。现在除了风就是雪,我什么也看不见。道布尔吉早就说过骆驼和马认识路,我们刚来的那天车陷在雪里,道布尔吉骑着马赶来救援,他松开马缰绳,马就自己跑回家了。 风把雪吹成一道道雪丘,这些雪质地坚硬,爬犁浮在雪面上滑行,骆驼则吃力地在雪里跋涉。骆驼边走边给自己喊着号子,骆驼的叫声和风声形成奇怪的应和。 四周一片洁白,太阳是唯一的参照物,我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道布尔吉用9张羊皮缝制的皮袍确实暖和,让我可以在零下0多度的严寒里坐在爬犁上保持一动不动。我们的影子不慌不忙地在后面跟着,城市里的影子被脚印踩扁、被车轮辗碎、被楼房和建筑物折断,此刻在如此洁白、平坦、广阔的空间里影子迅速恢复壮大,每当翻过一个雪丘的时候影子就挣扎着想要站起来。 骆驼的脚步和嘶吼变得急促,我正胡思乱想骆驼已经纵身一跃带着爬犁飞进了芦苇丛。一些“咔嚓”、“咔嚓”声在身后响起,无数杆芦苇瞬间将影子切割成碎片。太阳是始作蛹者,我长时间盯着雪和太阳看,眼前一片昏暗,太阳在幽暗里发出绿色的光芒,一枚带着巨大日晕的绿太阳好像骑了一辆独轮一样在无边的雪原上与我们并辔而行。绿太阳的照耀下,树木一样高大的芦苇迅速绿了起来,道布尔吉问我,你们那里野生动物多吗?我不知道他这么问是什么意思,我小心翼翼回答他说,不太多。我试探着问他,你们这儿有打猎的吗?道布尔吉说,我们不打它们,我们把它们当做兄弟姐妹,你们的人(汉族人)来打,都快打没了。我问道布尔吉,湿地里有鱼吗?道布尔吉说有哇,有鲫鱼、鲤鱼,鲫鱼和鲤鱼是同一种鱼吧?我被他逗得哈哈大笑,我说鲫鱼和鲤鱼的区别在于,鲫鱼比鲤鱼好吃。道布尔吉又说了一句令我羞愧的话,他说,我们不吃它们,它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我觉得我不能老是一动不动,我清清了嗓子活动了一下胳膊腿,我咳嗽出来的声音立刻被风声淹没,这些风大吼着好像要告诉我们什么。 道力玛说呼伦贝尔这几年太旱了,秋天的饲草储备不够,牲畜吃不饱,她家的羊群已经送到乌兰浩特去了。不光是她家,整个鄂温克草原的羊群都用车拉到多公里外的乌兰浩特草原去放养了。 我在单一的风景里昏昏欲睡,我准备站起来走走,但是我发现我穿着道布尔吉用9张羊皮做的袍子简直寸步难行。这时候我才想起来,我们大年初二来到鄂温克草原的锡尼河西苏木,中途车陷进雪里,道布尔吉骑着马从远处赶来,聪明的道布尔吉早就事先在附近电线杆底下的雪里埋了一把铁锹,他骑着马又扛来一把,两把铁锹挖了半天才把车从雪里挖出来。这天晚上道力玛来我们毡包说原本大年初二是草原上出嫁的姑娘回娘家的日子,但是由于我们的到来耽误了他们一家的行程,他们一家准备初三一早回娘家,问我们去不去。 我说去,道力玛说回娘家必须穿上正式的蒙古袍,但是我穿上道力玛的袍子捉襟见肘,于是我只好穿道布尔吉的。我穿上道布尔吉用9张羊皮缝制的袍子,道力玛将一条与我脖子上的紫色围巾相配的紫色腰带系在我的腰上,道力玛说腰带要系紧些,这样才暖和。于是我们的两架骆驼爬犁就出发了。 想明白这些我们已经到达四方山了。黑瑙嗨兴奋地汪汪大叫,道力玛的阿爸将我们迎进屋去,老阿爸看见我穿了一件男人的袍子忍不住乐了,道力玛的额吉则假装没看。午饭是布里亚特包子,没有菜。几天来我们吃到的唯一蔬菜是白菜炒木耳,道力玛说小卖部离得太远了青菜运到家已经冻了,这两颗白菜还是听说我们要来特意从旗里买回来的。道力玛说他们已经习惯了,在牧区为防止草原土壤沙化严禁开荒种地,哪怕种垄葱也不行。 吃过布里亚特包子我提议去拜访那位风语者,屋子里顿时安静下来,人们面面相觑。停顿了几秒钟之后老阿爸说,我就是。我大吃一惊,真想再吃两个包子压压惊。老阿爸将一杯桦树汁和草药混合酿制的浓烈饮料端到我面前说喝下去就能如我所愿,于是我毫不犹豫仰头一饮而进。我迫不及待想要检验一下效果,我穿上老阿爸轻便的短皮袍戴上尖尖的布里亚特魔法帽一头扎进风里。 刺骨的寒风像刀子一样扎在我脸上,我觉得晕头转向。我看见雪不知为什么变成了蓝色骆驼变成了红色,我与卸掉爬犁休憩的骆驼仿佛置身于海底。太阳周围出现了7个首尾相接的巨大日晕,我们刚刚抵达时老阿爸就将这些日晕指给我们看。这些巨大的光圈好像七彩的肥皂泡一样手拉手叠套在一起,太阳在这些光环里显得夺目异常,好像天空中的一枚巨大的钻石戒指。 是谁将雪变成了蓝色将骆驼变成了红色?是谁打开了天空之戒?难道是老阿爸的饮料?我妄图将这巨大的天象尽收眼底,我跌跌撞撞不断在雪地上跑来跑去调整位置,两匹红毛骆驼远远向我投来悲悯的一瞥。 我醒来的时候正躺在道布尔吉家的毡包里,炉子里的牛粪火着得不紧不慢。我问我的室友,我们去四方山了吗?她说我们已经回来了。风依旧高调地在外面跑,我说这些风说什么呢?我的室友说这里的风说布里亚特蒙古语我们怎么能听得懂?我想了想觉得有道理。我决定出去走走,我看看这些说布里亚特蒙古语的风到底在嚷嚷些什么。 我推开毡包的门,我被从来没见过的瑰丽夜空包围,无数颗宝石一样大而明亮的星星挤在我头顶的黑绒布上。星星们突然都长大了,以前它们生活在远处,现在它们从很远的地方跑出来看我,毕竟这个地方人少。有的星星还是排着队来的,它们三个一排五个一竖,我觉得这片星空如此新奇与似曾相识,但此刻我不能思考。我将永远铭记这片星空。离开这里一段时间后有一天我突然想起,那些星星排列的图案与我们的祖先在《河图》、《洛书》里排列的图案何其相似,难道那些讲布里亚特蒙古语的风就是要对我说这样一件事情? 彩虹衣裳草努力将自己举高,等到这些草突然开出花来,草原从此睁开了眼。无数朵五颜六色的花瞪大无数只五颜六色的眼睛,天和地一下子明亮起来。 如果它们不开花,我根本不认识它们。草原上的草像一群我不认识的人一样密密匝匝挤在我面前,我分不清它们到底谁是谁。等到草睁开花做的眼睛,我立刻就认出了它们。柠檬黄的野罂粟与萱草有很大区别;开蓝花的有鸢尾、翠雀、桔梗、勿忘我、齿叶沙参与矢车菊;金莲花的花朵和它的名字一样,尤如一朵朵小小的金色的莲花;细叶百合植株矮小花色鲜红,斑点百合植株高大花朵橘红。 草用花的眼睛看见,花都看见了什么?清晨刚下过雨,大地散发着梳洗后的香气。我学着一朵花的样子躺在草地上,四周野罂粟和萱草正开得密密麻麻。这是花的视角,不是我的,我的视角与天空成不同角度夹角,花的视角与天空大地平行。 我很少有机会躺在地上看天。我小时候有一次躺在家里借来的一辆小推车上,这辆木板做的小车刚好装下小小的我,我并不是要躺在上面看天,我设想有人能拉着车载我在院子里跑两圈儿兜兜风。但是我的想像没能得逞,我静静地在小推车上躺着,我在眨眼闭眼间发现院子、房子、大地一切都没了,我的眼前只剩下蓝天和白云。我被眼前的幽蓝紧紧攥住无法自拔,云彩在天空掠过,我在云彩间游过,我无力挣扎只能眼睁睁任由自己向那个幽深的蓝洞越坠越深越坠越远。最后我吓得一激灵,差点从车上掉下来。 现在我像朵花一样躺在花丛中,我像所有花一样与天空对视。野罂粟与萱草的花朵比我的头高出三到五厘米。我看到草把根扎在大地上,它们的花朵却开在天空上、开在云彩里。天空何其高远,花朵在风中摇曳,花朵和云彩一起向着天空更深更远处流浪,花朵见过我们没见过的更高远的天空。百灵鸟飞来把远方的事情讲给花朵听,百灵鸟讲话的声音像唱歌。每一朵花的伫足都怀抱蓝天与大地的喜跃。 这片山谷是海江家的草甸子。这是个口袋形的山谷,海江家的出牧点儿坐落在山谷入口处。以前这个出牧点儿属于俄罗斯人阿那托利,后来阿那托利回了俄罗斯,海江两口子成了它现在的主人。 海江两口子对这片山谷了如指掌,越过宽阔的麦地和油菜地,跨过一条暗河和狭窄的鹿道,金莲花正开得金光万丈。现在长麦子和油菜的地方以前开满了金莲花,如果没有这些麦地和油菜地这里将是花的海洋。虽然油菜也开花,但是它们和麦子一样,它们穿着同样的制服,高矮胖瘦全都一个样,好像一支军队踏着整齐的步伐野蛮地开了进来。海江嫂子指着远处另外一片金莲花说,那里明年将要开垦。而眼前这片麦地与林缘之间十几米宽的狭长空地已喷洒了除草剂,翻地的犁正整装待命,这些正在枯萎死掉的草,正是那一大片金莲花海仅存的孑遗。 芍药开在最远的南山坡上。芍药的命运类似于发菜与黑枸杞。以前碗口大的野芍药开得漫山遍野,后来无数人涌了进来,他们带着简易帐篷和炊具驻扎在山林里将数不清的芍药挖走。被掘开的深坑日益沙化,芍药根被大卡车一车一车地运往河北安国药材市场。这几年查得紧,大卡车变成了农用车、皮卡、轿车和面包,芍药根依旧在源源不断地往外运。这个地方人口少,即使所有人都跑到山上去看着这些芍药也看不过来,芍药只能越逃越远,最后逃到了深山里。 南山坡的芍药越来越少。海江家的出牧点儿是进出南山的必经之路,海江密切监视着这些盗贼的一举一动,但他既未报警也未出面制止更没有挺身而出将他们轰走。海江在处理这件事上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第一那片草甸子不是自已的;第二怕被报复。今年挖芍药的人没来,海江得出的结论是,芍药已经被挖没了,所以他们不来了。海江很高兴,如果这些贼再也不来了,那么再过几年残存于地下的芍药根又会重新萌蘖而出。但是这伙儿贼不来别的贼也会来,虽然人类社会已经用建设生态文明对前三次工业革命做出了忏悔与救赎,但这个古老民族几千来构建起来的价值精神体系正在癫狂到登峰造极的金钱崇拜下支离破碎土崩瓦解,古老的农耕文明正堕落为贪婪与利欲熏心,将个体的生存发展凌驾与自然与人类共同命运之上,滥挖野生芍药如是,过度开垦亦如是。 山谷里空无一人,大地已经为它们分配好了,每一种花管理一个地方。我在开满金莲花的土地上看到火红的山丹和蓝色的桔梗,大山丹和桔梗长到一人来高,好像它们是吃饱喝足来走亲戚的;东山坡的白桦林下一片蓝色的翠雀倾斜着向上生长,好像一群穿蓝衣服的人正弓着腰准备到白桦林里去;狍子住在开满金莲花的树林里,我们的出现将两只狍子惊得跳起,它们跑到树林里躲在一株白桦后好奇地向我们张望。远处紫色的千屈菜、草本威灵仙、轮叶婆婆纳、大花葱、大叶龙胆与粉色的石竹、野火球、亚洲百里香、盘龙参、佛手参、野豌豆、白色的银莲花、天目琼花、玉竹、繁缕、黑水罂粟与黄色的汉三七、龙胆、柳兰等等交织在一起,好像给大地穿上了一件彩虹做得衣裳。 淹没在盛开的野罂粟与银莲花中的海江家的出牧点儿如同花海中的一叶小舟。海江家的出牧点儿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能开0万块钱的奶支,后来奶站不收奶了,白花花的牛奶不得不一车一车倒掉。以前养牛户将牛撒在草甸子上散养,后来政府要求集中起来养,养牛户不买帐,很多人因此而不养牛了。有那么几年,牛奶被倒掉,奶牛被卖掉,我小时候就常听说奶站关关停停,不过最近我听说奶站又开始收奶了。 黄花菜(萱草)盛开的时候我们来到海江家的出牧点儿上,海江说他家出牧点儿附近生长黄花菜的那片草甸子早就被生产队翻了,他开车带我们去往另外一位牧户的草甸子,但依旧所获不多。过了几天我们决定再去九队的草甸子碰碰运气。所幸那片草甸还在,草甸上的黄花菜也正开得气势恢弘。以前这个季节家家院子里铺满了晾晒的黄花菜,我已经有好几年看不到这种情形了。我母亲说,40年前她两个小时就能撸两麻袋黄花菜。她用了“撸”而不是“采”,她说那时的黄花菜堪比现在的油菜花海,她只需一手撑住麻袋,另一只手的五个指头叉开像一把铲子一样沿着花萼部分一捧一捧往麻袋里收即可。 我们采黄花菜的时候我父亲说他记得这附近某处生长着东北藏红花,但他找了一下午也没找到,不知是他记错了位置还是原先长藏红花的地方已经变成了麦地和油菜地。 这片草原属于世界上种群结构最丰富、种类最复杂的草原,俗称“开花的草原”。我没有福份见识草原40年前的盛景,但即使大地赐予的这件彩虹的衣裳已在所难免地日渐斑驳,额尔古纳这片草原依旧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草原。那么再过40年呢? 诗人在牧区,人人都是诗人。牧民与农民不同,农民的目光被身边的高楼大厦和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魇住,他们的眼睛和心灵很难再到达其它地方。在牧区,除了天就是草,牧人的毡房扎在天堂与草原之间,天鹅和苍鹭在河套里翩翩起舞,牛马羊群像散落在碧玉上的珍珠,每天面对这样的情形,即使是傻子也不能无动于衷。 一个诗人一辈子能写多少诗?如果将这些诗写在A4纸上装在50斤装的面袋子里,能不能装满一面袋子?或者能装几面袋子?我听说通拉嘎和他写的一面袋子诗的时候就忍不住这样想。 那些诗像水一样从通拉嘎的脑袋里汩汩流淌出来。通拉嘎夜以继日的写,他骑在马背上写,坐在草地上写,躺在毡房里写。他的脑袋里装满了诗,一个人的脑瓜被一样东西塞满就很难再塞进其它东西,这导致通拉嘎除了写诗以外老是干不好别的事情,比如高考他没考上大学,比如他放牧的羊群老是走丢。后来他去苏木帮他姐姐看商店,他无时不刻不沉浸在自己的诗里,他被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日用杂贷搞得头昏脑涨,他接手一年半载之后,原本好好的一个苏木杂货店就开始入不敷出,濒临倒闭。 在牧区,随手拽下几朵云彩就能涂抹成一片诗的牧民比比皆是,他们把阳光和马蹄声挂在草叶子上、把漫天风雪和牛粪火着成的炊烟刻在露珠上、把大雁、狗和牛马羊的叫声埋在月光底下,等到岁月踉跄了轮回,他们把这些日子风干成的句子采摘下来,一片一片雪片一样堆在自己的毡房里。后来写诗的牧民越来越多,草原上成立了诗歌那达幕,每位牧民诗人都可以在诗歌那达幕上大声朗读自己的作品,然后再评出一、二、三等奖来,赛诗成了和骑马射箭一样的竟技比赛项目。 通拉嘎没赶上这样的好时候。他赶上的时候还没有网络或网络还不够发达,更何况是在草原深处,没有博客、微博、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nhukb.com/wqbbbq/8519.html
- 上一篇文章: 结节息肉囊肿,体检查出的这些ldq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