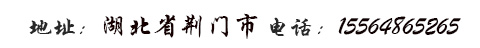人性档案系列这个村的婴儿,都活不过7个月
|
你们好,我是胖胖。 今天继续给你们讲表姑云游时,亲历的奇闻异事。 在一天临晚的时候,他们三人走到了一个处于深山里的小村落,里面约有三五十户人家。 坐在表姑肩膀上的吱吱一进村就显得烦躁不安,连一向嬉皮笑脸的周春也变得神情严肃起来,这让表姑心里暗暗觉得这个村子肯定不简单。 然而没想到,就是在那天夜里,表姑第一次“见了鬼”。 我们走进村子,敲开了一户人家的大门,提出想要借宿,一个精瘦的老头把我们迎进了屋。 老头的老伴儿看起来也是干干瘪瘪的,光着上身,胸前提溜着两条蔫茄子似的乳房,下身只围了一条脏兮兮的破布。 她颤巍巍地为我们三个倒了三瓷缸热水。 师父和周春端起茶缸,小口地啜着。 我盯着茶缸壁上黑黢黢的污垢,连手都不愿碰它。 老头此时正张罗着兄妹三个把房间让出来给我们住。 他家里只有两间屋子,进门就是老两口的卧室兼厨房兼客厅,侧面一间小屋,住着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年龄最小的女儿也有三十多岁了,怀里抱着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 我本来以为师父会推辞,没想到他连头也不抬一下,只是面色平静地稳坐不动。 我那小娃娃大师兄也和师父一样,稳稳地坐着。 我心里有些气,但没敢说什么。 老太太为我们仨收拾好了床铺,我躺在他们家的硬板床上,心中升起一股莫名的烦躁,无论如何睡不安心。 正翻来覆去的时候,身旁的大师兄突然问我:“喂,你发现什么了没?” “发现了,良心不安的时候人会睡不着!”我气呼呼地怼了回去。 大师兄噗嗤一笑:“孩子哪儿来的?” “什么孩子?”我没好气地问。 “那女人怀里的孩子,哪儿来的?” “自己生的呗,还能哪儿来的?” “那女人骨盆未开,是个老处女,哪里能生孩子了?” 我一怔:“小小年纪,怎么连这个你都知道?” 大师兄的语气突然严肃了起来:“这里就两间屋子,咱们可都看遍了,也没见着这家儿媳妇,你说怪不怪?” 我心里颤了一下,仍然嘴硬:“死了跑了出门了,有什么稀奇的?” 但我知道,那小孩一看就是还没断奶的,一刻也离不开母亲,我嘴上说的理由,全都站不住脚。 大师兄神神秘秘地说:“那你就等着瞧稀奇吧。” 我心里又多了个疙瘩,更加睡不着了,索性睁着眼,盯着房梁上吱吱的尾巴出神。 不知过了多久,隐隐从窗外传来断断续续的哭声。 我竖起耳朵细听,那哭声逐渐变得越来越清晰,只是忽远忽近、飘飘渺渺的,不知到底是从哪里传来的。 那似乎是个女人的哭声,又尖又细,悠远绵长。 我听得背上的毫毛都竖了起来,一股寒意从脚底窜了上来。 我推推身边的大师兄:“你听到没?” “嘿嘿,稀奇这就来了。”大师兄还没经历变声期,他尖细的嗓音在这时候听来,跟屋外那女人的哭声差不多。 忽然,“哐”地一声巨响,我们的屋门被人撞开了,两个男人冲到我们的木板床前,“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大师,求你救救这孩子吧!” 我被吓得跳了起来,却见床前跪着的是老头的两个儿子。 大儿子手里抱着那个婴儿,随后跟着过来的是老头、老太太和他们的女儿。 那婴儿此时没用襁褓包着,赤裸着的小身体发出青紫的诡异颜色,婴儿的眼角挂着泪珠,正艰难地瞪着腿,像是想哭又憋着气哭不出来。 正坐在床尾入定的师父慢吞吞地睁开眼,又慢条斯理地整好了自己的衣衫,这才走下地,掰开婴儿的眼睑瞧了瞧,转头对大师兄说道:“是时候了。阿春,童子尿。” 大师兄应了一声,也不避人,就在床头找了个空碗,冲着碗里撒起了尿。 我脸一红,尴尬地撇过头去,见师父从包袱里取出一张黄纸符,念了几句咒语,再用右手食指和中指顺着纸符一划,那纸符“呼”得一下就起火烧成了灰烬。 大师兄恰好在这时递上自己那碗童子尿,师父右手食指和中指上沾着纸灰,混在童子尿里搅动一圈,便用食指点在那婴儿的喉咙上。 师父这一指点过,婴儿的喉咙上便现出了一片胎记似的血淤。 婴儿立刻哭出了声,皮肤上森森的青色渐渐散去,又露出原本粉嫩嫩的肤色。 师父的中指顺势在婴儿胸口及肚腹上弯弯曲曲画了一道符咒,画毕,屋外那似有似无的女人哭声,霎时也没了声。 老头一家五口人见婴儿保住了性命,磕头如捣蒜一般。 我多嘴问了一句:“你怎么知道我师父能救你家小孩儿?” 老头带着哭腔道:“我们是没办法才来求大师的。村里的小孩都是没病没灾的,可活不到七个月就突然没了,眼看着今儿就轮到我孙子了,大师恰在这个时候出现,世上哪有这般巧事?” 师父沉着脸说道:“老道向来不救不义之人,今晚施法救你孙子,已经是破例,你须老老实实告诉我,这婴儿的生母是谁?” 老头脸上变了色,犹豫道:“这……这个……” 师父冷“哼”一声:“老道这一符,只能保这婴儿三天的性命。三天之后,他还能不能挺得过,就全看你了。” 老头的二儿子忽然站起身:“爹,这事不能说。” 老头的女儿也小声说:“爹,要让村长知道了,咱家可就完了。” 老头唉声叹气,看看儿女又看看我师父,不知作何决定。 大儿子缓缓抬起头,语气坚定地道:“不能让老吕家没了后!你们都出去,我来说,村长那边,我一个人顶。” 二儿子红了眼,一屁股坐在地上,不走。 老头望望两个儿子,一咬牙,老泪纵横:“既然敢做,就没什么不敢说的!孩儿他妈,是山外面拐来的女学生,这兄弟俩同趁一个,怕跑了,现在就在屋后面红薯窖里关着。” 我的脑子里“轰”得一下,从前只是听说过这种事,现在真让我碰见了。 师父厉声道:“带我们过去!” 老头把我们带到了红薯窖前,放下梯子,大儿子一声不吭地下了窖,把拐来的女人背出来。 女人还光着身子,全身都是脏兮兮的污泥。 我的泪水忍不住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急忙脱下自己的大衣,给她披在身上。 女人神色漠然,恍如未觉。 师父示意我把女人搀到他面前,他冲着女人耳语几句,只见女人苍白的脸上忽然有了血色,两眼也放出了光彩。 我感到她的力气也忽然回来了,跟刚才简直判若两人。 师父叮嘱大师兄回屋取了他的桃木杖,又解下自己腰间的铜铃,一同交给女人。 女人感激地向师父鞠了一躬,转身离去。 老头的二儿子还想追上来抓那女人,我叉腰拦在他面前,恶狠狠地瞪着他。 他推我的手伸到一半,终于又神色黯然地退了回去。 师父问:“村里有几户人家里的女人是拐来的?” “就这近十年来,村里男人娶的婆娘都是从外面拐来的,得有二十多户……山里人穷,女儿嫁不出去,男娃又娶不来媳妇,想保住香火,只能靠这种手段。”老头嗫嚅地回道。 二十多户,就是二十多个年轻女孩! 这十年来,她们陆陆续续被拐进这个小山村里,遭受着非人的折磨和凌虐,充当着毫无情感的生育机器。 这种场景我根本无法想象!我的指甲掐进了肉里,心里头一阵一阵地抽搐。 “新生儿活不过七个月,这种状况持续了多久了?”师父又问。 大儿子说:“具体时间不知道,差不多就是这两三年的事。” 师父点点头:“把老道救你儿子的事,跟村里人宣扬宣扬,说老道我有法子渡他们的七月之难。阿春,素素,换上法衣。” 我一边手忙脚乱地从我的行囊里找法衣,一边问道:“师父,咱们干嘛去?” “看坟。” 我的动作一顿:“现在?半夜?” 大师兄踢了我一脚,还对我扮了个鬼脸:“胆小鬼!” 我和大师兄换好绣着八卦阴阳的粗布道服,跟在师父后面,出了老头家的屋门,摸黑行走在山路间。 附近每有一点风吹草动,都让我的心脏“扑通扑通”狂跳一阵。 大师兄“嘿嘿”笑着:“胆小鬼,多跟吱吱学学。” 吱吱这会儿正把尾巴盘在我的脖子上,安安静静地坐在我的肩膀上,多少让我感到了一点暖意和安全感,这时,我也不嫌弃它一直把我当它的“坐骑”了。 师父的脚步慢了下来:“你们在这里等着。” 我和大师兄应了一声,便找了路边的缓坡坐下,等师父回来。 我不由得有些好奇:“山里这么黑,师父能瞧得见?” 大师兄说:“师父是用脚‘看’的,不是用眼看的,师父在丈量坟地的排布。” 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我们俩一直等到天色渐渐发白,还没等到师父回来。 这时我才发现,我昨天坐了一晚上的“缓坡”竟是一座新起的坟头,亏我还百无聊赖地抓着旁边的土块扔来扔去。 我顿时像屁股着了火一样,弹跳着站起来。 大师兄笑得前仰后合,原来这小子早就知道这里是坟堆。 不久,山里面的晨雾渐渐散开,我的眼神所及,竟然全是一堆一堆的坟头! 我差点把下巴惊掉。 想想昨天晚上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待了一夜,不禁有些后怕,一丝冷汗顺着我的脊背淌了下来。 我抬头看到师父就在我们前面三四百米远的地方,一面迈着非常缓慢的步子,一面弯腰用树枝在地上画着些什么。 这时,有一队村民气势汹汹地冲进了坟地,当头那人冲我们大叫:“快滚快滚,吕家沟的祖坟岂是你们能随便进的!” 师父那边还没好,我直了直腰板,把大师兄护在身后,挡在村民面前。 当头那人是个身材壮实的黑脸男人,看起来约莫五十多岁,他毫不理会羸弱的我,伸手就把我推了一个趔趄。 大师兄撇着嘴问:“吕家沟两年半都没有新生儿活下来,看你们这样,是想整个吕家沟都绝后吗?” 别看大师兄小小年纪,但说起话来却有板有眼,身子一正,竟带着几分威严。 乱糟糟的村民陡然安静了下来,打头那黑脸男人眼角的肌肉颤了颤,恶狠狠地说:“别以为吕老赖跟你们说些乱七八糟的鬼话,你们就能在这儿装神弄鬼了。” 大师兄不甘示弱:“两年半之前,村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黑脸男人的神色大变,握着拳头怒喝:“赶紧滚蛋!再不滚,小心我们打死你们这三个狗道士!” 黑脸男人的话刚说完,师父的声音忽然响了起来:“婴儿夭折的原因,老道已经找出来了,是跟一个两年半前死去的女人有关。” 一众村民面面相觑,黑脸男人抿了抿嘴,强自道:“胡说八道。” 师父平静地擦了擦额头的汗珠,走到黑脸男人面前,不紧不慢地说:“你是村长?先别忙着否定老道。” 不等那黑脸男人回应,师父便又对着一众村民说道:“老道与村长打一个赌,若老道帮你们解决了婴儿夭折的问题,就请村长作主,将村子里诱拐来的女人全部放走,且以后不再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若老道解决不了,我们师徒三人,便任凭村长处置。” 黑脸男人表情阴鸷:“放屁!哪来的诱拐……” 师父打断了他的话:“各位意下如何?” 黑脸男人身后的村民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说话,似乎都在衡量师父开出的条件。 大伙儿犹豫了好一阵,忽然有人开头道:“别人我管不着,如果道长能让俺家小六子活下来,我那拐来的婆娘,我亲自给她送出山去。” 说话的这男人,已过了五十岁了,他儿子几天后就要满七个月了。 他这年纪能有个儿子,实在是太难得了,生怕孩子真的夭折。 这话一出口,其他人也不等村长表态了,纷纷表示愿意。 见到这阵势,黑脸男人虽不再反驳,却也狠狠地盯住师父的眼睛说道:“那好,就这么定了!” 村民按照师父的要求布置好法台,我和大师兄一人腰间围了一条红绸,盘腿坐在用香灰围成的圈子里。 大师兄告诉我,红绸是拴魂绳,香灰圈是护身的阵法,这两样东西能保住我们的命。 一切就绪后,太阳已经隐在山后了。 当天色完全黑下来时,师父点燃了法台上的红烛,开始念咒作法。 这时,山风突然凛冽了起来,吹在我脸上,像刀割一样。 大师兄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把铁质八卦,塞到我手里:“你道行太浅,今晚的阵仗怕你吃不消,把这个八卦抱好。” 我感激地点了点头,接过八卦才知这玩意儿冰凉透骨,又重的要死,心想大师兄肯定又在对我恶作剧。 但是保命要紧,这种危急关头,我还是宁可选择相信他。 山风一阵强过一阵,风中又传来昨晚尖细绵长的女人哭声。 这次却不再飘飘渺渺似有似无了,而像是真有一个女人扒在肩头,哀怨地哭泣一样。 我的神思已经凝聚不起来了,只觉得风吹得我四肢冰冷,快要冻僵了。 树梢上似乎又有猫头鹰沉闷的叫声。 我下意识地站起身,想要去找那只猫头鹰在哪儿。 突然,一阵巨大的铜铃声在我耳畔炸响,震得我耳朵生疼。 我手里捧的那个又重又凉的铁八卦,中间连着轴的阴阳鱼正疯狂旋转着,居然传来了暖融融的感觉,就像是个小火炉。 我回过神,发现大师兄正拉着我腰间的红绸,而那股妖风不知何时已经停了。 我冷汗直流,刚刚实在是太险了,我不知不觉间,险些被那只猫头鹰的叫魂声给勾走了。 这时候,我看到法台前缓缓走过来一个穿着时尚的年轻女孩儿,师父先前叮嘱过村民,千万不要靠近坟地来,否则性命堪忧。 我正要出声喝止,大师兄急忙按住我的嘴巴:“你看她有什么不对劲吗?” “没什么不对劲的啊,就是这个装束,不太像是山里人……”我跟着大师兄的话,细细打量那个女生,“啊!她没有影子!” 我浑身一颤,惊的嘴巴一张一合,那个女孩在烛光的映照下,居然显不出影子! 女孩儿就在这个时候开口了:“道长的法术确实厉害,但这村庄的事,你们也别想插手!” 师父笑了笑,对那个女孩儿道:“我们是来帮你的。” 女孩儿的眼睛转向别处,怨毒的声音响起:“帮我?哼,你让整个吕家沟的人断子绝孙就是帮我!” 师父问:“为什么对他们这么大的怨恨?” “我和妹妹出来爬山探险,被村长骗到他家里,整整三个月都被他关在阴暗的小屋里侮辱。 我妹妹才16岁啊!我逃了出来,想找帮手救我妹妹,谁知道,这一整个村子的人都是禽兽! 这群禽兽不是想要儿子吗?那我就让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死掉!让他们断子绝孙!” “可是婴儿无罪,怀孕的女人更是无罪。第一个孩子死了,他们还会逼迫那些女人生第二个、第三个,你这样做,岂不是让让那些婴儿和跟你一样遭遇的女人遭受更大的伤害?” 女孩儿冷笑:“难道就这样放过这一整个村子的禽兽吗?” “难道还要让跟你同样命运的女人继续受苦吗?”师父反问,“老道可以搭救她们,你只管安心转世,到时天道自彰。” 女孩儿的表情阴晴不定,最后似乎是相信了师父的话:“好,道长,我信你一回,不过,我要等到你说的天道昭彰以后再离开。” 师父点点头。 女孩儿的身子隐藏在山雾之中,渐渐消却。 我们下山去找那黑脸男人村长兑现承诺,他却立刻让人把我们关进了他家偏房。 我气得跳脚,骂了他祖宗十八代,喊得嗓子也哑了。 大师兄帮吱吱逮着虱子,笑我说:“傻师妹,你说你这么大一个人了,怎么就这么沉不住气,来,坐下歇着。” 我哑着嗓子愤愤不平:“他们不兑现承诺,还把我们关起来,你们怎么还坐得住?” 大师兄说:“师父神机妙算,早就知道是这个结果了。” “哦?”我不解,“那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办?” “靠过来,我告诉你!”大师兄神神秘秘地回答。 我依言把耳朵贴过去,他突然对着我耳朵大声喊:“天机不可泄露!” 如果不是因为他是我大师兄,我早揍他了! 我们仨在村长家的偏房饥一顿饱一顿地度过了五个日夜,再没听到过那女人的哭声了。 我猜村民们肯定都知道师父的灵验了,但村长还是不愿放我们走。 到第五天清晨,外面传来一阵急促且刺耳的鸣叫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 我迷糊了几秒钟,忽然激动地跳了起来:“那是警鸣声!警察来救我们了!” 我们先前救走的被吕老赖家拐来的女人,借着师父的桃木杖和铜铃引路,在黑夜里成功逃出大山,报了警。 警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调集了大批警力,借着清晨山雾的掩护,包围了整个吕家沟。 吕家沟作恶、助恶的人,没有一个漏网,全部被抓了起来,等待着被定罪。 村里二十四个被拐来的女人,终于能够离开这个恐怖、野蛮、落后的小村庄了。 我沐浴在久违的阳光之下,心底却忍不住震颤不已:“世间不知还有多少像这样的地方,依旧被罪恶的阴霾笼罩着呢?” 师父微笑:“太阳能照到的角落,天道就会彰显。罪恶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尚处于黑夜之中,耐心些吧,太阳终究会升起,恶人终究会受到惩罚。” 完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nhukb.com/wqbbtx/8384.html
- 上一篇文章: 这些动作可以让宝宝变聪明012个月宝
- 下一篇文章: 1到6个月的脑瘫宝宝,会发出12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