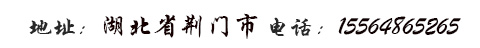壁画ldquo叉手rdquo
|
“叉手”礼图像考 黄剑波 上海大学数码艺术学院(讲师)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摘要:“叉手”礼,系揖礼的一种,分佛教“叉手”礼和世俗“叉手”礼两种表现形式。佛教“叉手”礼,历史文献多有记载。关于世俗“叉手”礼图像信息,诸多学者认为见于宋元以后。本文通过对晚唐()赵逸公墓、五代()王处直墓以及宋、辽、金壁画墓中的“叉手”人物图像进行梳理和比较分析,同时结合历史文献与传世绘画作品图像信息进行考证,认为世俗“叉手”礼最早出现于宋代的结论欠妥。“叉手”礼图像应该在唐和五代时期就已经出现,并已经成为当时流行的常用礼仪。 关键词:“叉手”礼图像赵逸公墓王处直墓 一、魏晋六朝之前“叉手”礼多见于权贵之礼 中国自古为礼仪之邦,《礼记》载:“夫礼者,自卑而尊人”。其中有一种“叉手”礼,古老而独特。许慎《说文解字?又部》说:“叉,手指相错也。从又,象叉之形。”顾野王《玉篇?又部》:“叉,指相交也。” 《汉语大词典》解释“叉手”是佛教一种敬礼方式,“两掌对合于胸前且交叉手指”。《禅宗词典》认为:“手掌相合,手指交叉,表示心诚专一的礼貌动作。” 西晋竺法护于泰康七年()于长安翻译《正法华经》10卷,其中《正法华经·应时品》:“于是贤者舍利弗,闻佛说此欣然踊跃,即起叉手白众祐曰:今闻大圣讲斯法要,心加欢喜得未曾有,所以者何?”。 《持心梵天所问经·明网菩萨光品》:“于是明网菩萨,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叉手,稽首佛足。” 蒋宗福、李海霞译注禅宗史书《五灯会元》认为:“交叉手指合十。” 以上可见,佛教“叉手”礼的主要特点是手掌相合,手指交叉。 “叉手”不仅是一种佛教礼仪,也是一种世俗常用礼仪,属揖礼的一种。特别在汉末魏晋,“叉手”礼多次见于史册。《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记载当时隗嚣割据陇右,马援给其部将杨广写信说:“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义,内有朋友之道,言君臣也,用当争谏;语朋友也。应有切磋。岂有知其无成,而但萎腇咋舌,叉手从族乎?”《后汉书·灵帝纪》载:“(张)让、(段)珪等复劫少帝、陈留王走小平津。尚书卢植追让、珪等,斩数人,其余投河而死”。李贤注引《献帝春秋》资料说:“(张)让等惶怖,叉手再拜叩头,向天子辞曰:‘臣等死,陛下自爱。’遂投河而死。” 《三国志》卷八《公孙度传》注引《魏略》曰:“故公文下辽东,因赦之曰:‘告辽东、玄菟将校吏民:逆贼孙权遭遇乱阶,因其先人劫略州郡,遂成群凶,自擅江表,含垢藏疾。冀其可化,故割地王(孙)权,使南面称孤,位以上将,礼以九命。权亲叉手,北向稽颡。……’”同书卷二十八《邓艾传》议郎段灼上疏曰:“……艾受命忘身,束马县车,自投死地,……使刘禅君臣面缚,叉手屈膝。”“叉手”礼在魏晋六朝也相袭用。见于《隋书·经籍志》的《孔丛子·论势》云:“游说之士挟强秦以为资,卖其国以收利,叉手服从,曾不能制。” 上述史料中反复出现“叉手”礼,可见此礼在东汉及魏晋时期为常见礼仪,多见于权贵之礼。除李贤注引《献帝春秋》资料描述(张)让行的是实礼,其他主要为书信、诏书、文章等记录的虚礼。通过分析,见于文献中的“叉手”,其含义亦有区别,除表示敬、服从之意的特定握姿外,有合掌(此义多见于佛经)、垂拱(两手相交于下)、高拱(两手相交于上)、交手诸义。 探究这些史料中描绘“叉手”礼手形、动作的具体样式,因具体解说文字和直观图像资料的匮乏,难以窥见一斑。 有意味的是,年底,江苏江宁县张家山西晋墓出土“叉手”女陶俑一件。高19.6厘米、最宽10.4厘米。头发向后梳成小髻,目圆鼓,塌鼻,瘪嘴,耳垂上有饰,衣对襟长裙,曳地,不露足,宽袖,小臂裸露,双手置胸前。似作恭敬的“叉手”礼。但细致观察,该陶俑右手拘谨地半压在左手上方,双手紧贴在胸前衣襟上。从陶俑的装束、神情看,陶俑眼睛略圆,眼珠鼓起,突在眼睑之外,满脸惊恐之态,应该是受到训斥或受罚的仆从,不像是自然行礼之态。与后世唐宋时期能见到的“叉手”图像也迥然不同。因此,不能断定此动作就是魏晋时期“叉手”礼手法(图1)。 图1江苏江宁县张家山西晋墓陶俑 (采自:南京博物院:《江苏江宁县张家山西晋墓》,《考古》年第10期。) 二、唐、五代“叉手”礼形式成熟,普遍流行 (一)柳宗元、杨牢作诗与晚唐赵逸公墓壁画 北宋王谠的《唐语林》卷三载:“华阴杨牢,六岁人杂学,归误入人家,乃父友也,二丈人弹棊,戏曰:‘尔能为丈人咏此局否?’杨登时叉手咏曰……”。一个六岁孩童,作诗前很自然“叉手”施礼,充分说明这种礼仪已经非常普及,妇孺皆知。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在唐顺宗永贞元年()到唐宪宗元和十年()被贬永州期间,生活穷困窘迫。《新唐书·柳宗元传》记载:“宗元为邵州刺史,在道,再贬为永州司马,即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在《同刘二十八院长寄澧州张使君八十韵》诗中柳宗元写道:“入郡腰恒折,逢人手尽叉。”叙述他被贬永州屈身事人,低调生活的情况。永州之所以当时为流放戴罪官员之所,因其蛮荒偏僻,即“涉履蛮瘴,崎岖堙厄”。柳宗元在此地“逢人手尽叉”,一方面说明他不得不见人施“叉手”礼,到处摧眉折腰的窘境。同时也说明“叉手”礼即便在永州这种流放之所,也成为当时社交的常用礼仪。 柳宗元生于唐代宗大历八年(),唐宪宗元和十四年()病逝。杨牢生于唐文宗大和五年(),卒年不详。二人所行“叉手”礼具体动作样式如何? 年3月,在河南安阳发掘一座晚唐墓葬,据墓志记载,墓主为赵逸公。此墓建于唐文宗大和三年,即公元年,也就是柳宗元去世后的第十年。应该说赵逸公和柳宗元基本是同时代人,他去世时间和杨牢出生时间也相差无几。 赵逸公墓中有近30平方米壁画,壁画共有八组人物画和一组花鸟画,人物部分绘有十四女、四男共十八个人物,内容主要有更衣、训仆、侍女、劳作、休憩场面等。赵逸公墓室壁画中,出现了一站一跪两个仆从形象,对墓主人行礼,从手形及动作看,正是后来宋人所说“叉手”礼(图2)。 图2河南洛阳晚唐赵逸公墓“叉手”人物图像 (拍摄于河南古代壁画馆) 从此图可以看出,两人施礼动作与江宁张家山西晋“叉手”陶俑手式完全不同。左手成掌型,左掌外包右手,以左手紧把右手拇指,其左手小指则向右手腕,右手四指皆直,拇指向上。而且手很自然置于胸前,与前胸之间留有距离。 (二)“温八叉”雅号与五代王处直墓等墓室壁画 晚唐著名诗人温庭筠(约-),精通音律,其诗辞藻华丽,与李商隐齐名,有“温李”之称。词风浓绮艳丽,语言工炼,格调清俊,与韦庄齐名,并称“温韦”。 晚唐进士王定保(-)在《唐摭言》中记载温庭筠轶事说:“温庭筠烛下未尝起草,但笼袖凭几,每赋一咏一吟而已,故场中号为‘温八吟’。”北宋孙光宪在《北梦琐言》写得更详细:“温庭筠才思艳丽,工为小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时人号‘温八叉。’今人徵典,但知有‘八叉’,罕知有‘八吟’矣。”宋代尤袤《全唐诗话·温庭筠》记载也相同:“庭筠才思艳丽,工於小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时号‘温八叉’。” 不管“八吟”还是“八叉“,都是形容温庭筠才思泉涌,诗词创作速度快,可以比美曹植“七步诗”。 温庭筠的“八叉”一般认为是“叉手”,也有人认为是“笼手”、“抄手”,是把双手笼到衣袖里,就如同《唐摭言》中说的“凭几笼手”。但如果是“抄手”、“笼手”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是不符合实际情况。温庭筠“八叉”成名是“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均在考试时用,考试时不会时而双手笼袖,时而写字,显得过于琐碎杂乱。而且抄手在衣袖,时间节奏就不快,突出不了温庭筠才思敏捷的特点。 第二与杨牢的“叉手”旧事矛盾。前文提及王谠的《唐语林》记载杨牢故事,杨牢在吟诗前“叉手”,应该是施礼,绝不可能和后来的温庭筠不约而同,是抄手笼在衣袖里。因此,当时文人在作诗前,“叉手”施礼可能是一种修养和习俗,是对听众和考官的一种恭敬和尊重。 所以说,温庭筠的“叉手”应该是“叉手”施礼,以八次“叉手”礼来显示温庭筠成文时间之短,也说明这种“叉手”礼已经是大众熟知的礼仪。温庭筠“叉手”礼动作具体样式是怎样呢?从和他时间前后不远的五代王处直墓室壁画中,可以找到图像印证。 年7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会同保定市文物管理处、曲阳县文化局、曲阳县文物管理所组成的考古队发掘了五代王处直墓()。墓前室南壁下栏墓门东、西两侧各有男侍像一幅,头戴黑色翘脚幞头,身着圆领缺胯袍,腰束带,“叉手”侍立(图3)。东耳室北壁绘侍女童子图一幅,侍女梳高髻,额前插花,鬓部插白色梳子,身着红色短襦裙,内穿抹胸,下穿白色长裙,脚穿高头履。童子着圆领缺胯袍,腰系红带,着长裤,脚穿线鞋,“叉手”而立(图4)。 图3河北曲阳五代王处直墓前室南壁下栏东侧男侍图 (采自: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处:《五代王处直墓》,文物出版社,年,彩版四。) 图4河北曲阳五代王处直墓东耳室北壁侍女、童子图 (采自: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处:《五代王处直墓》,文物出版社,年,彩版四。) 另外,年,山西省太原市第一热电厂发现一座北汉墓(),甬道西壁绘一门吏,侧身面向墓外站立,双手拱手于胸前,怀抱一条两端露白的黑色杖杆(图5)。甬道东壁绘一门吏,其构图、服饰、动作、所持器物与西壁近似(图6),二者均施“叉手”礼。河南省新郑市陵上村后周恭帝柴宗训墓()也发现了“叉手”人物图像(图7)。 图5山西太原市第一热电厂北汉墓“叉手”人物图像 (采自:徐光冀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山西卷》, 科学出版社,年1月。) 图6山西太原市第一热电厂北汉墓“叉手”人物图像 (采自:徐光冀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山西卷》,科学出版社,年1月。) 图7河南省新郑市陵上村后周恭帝柴宗训墓“叉手”人物图像 (采自:徐光冀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河南卷》, 科学出版社,年1月。) 年,洛阳孟津县新庄村发现一座晚唐五代贵族墓,由于墓志丢失,墓主人很难确定。但从墓葬形制、壁画内容及出土器物推断,应为晚唐五代时贵族墓。该墓在甬道、墓室中均绘有壁画,墓道壁画保存完好。很清晰地看到两名侍者行“叉手”礼(图8)。 图8河南洛阳孟津县新庄村唐五代贵族墓“叉手”人物图像 (拍摄于河南古代壁画馆) (三)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天赞二年”墓室壁画 年10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阿鲁科尔沁旗文物管理研究所对赤峰宝山辽壁画墓进行发掘,此墓有“天赞二年”()明确的题记纪年。在1号墓前室南壁绘吏仆图,甬道入口两侧各绘一人。左为男吏,勾鼻,戴黑色幞头,着圆领紧袖紫褐色团花长袍,腰系白带,穿浅色便靴,“叉手”而立。从面容看,明显是契丹或是其他少数民族。另在石房内南壁东侧绘有男侍图,戴黑色幞头,面白,朱唇,着黑袍,白色中单,系红色锦带,白裤,“叉手”于胸前(图9)。 图9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叉手”人物图像 (采自: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鲁科尔沁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年第1期。) “天赞”是年二月到年二月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年号,年唐朝被朱温的后梁取代,离“天赞二年”不过短短十余年时间。而年又是朱氏后梁灭亡的“龙德三年”,也是后唐李存勖的“同光元年”,属于中原五代开始的早期。这个时期正是北方各个割据政权混战最激烈的时候,北方各民族正常的文化交流受到严重阻碍。因此,“叉手”礼传播到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偏远之地,一定是远远早于这个时期。这也证明了“叉手”礼出现的成熟性和广泛性。 结合前面资料看,柳宗元的“逢人手尽叉”是在湖南永州。依照《新唐书》、《旧唐书》、《唐才子传》等书记载,温庭筠一生的活动轨迹主要是在京师长安,间或在湖北襄阳和淮南一带,两者距离跨度数省。 从发掘的几座墓葬看,赵逸公墓建于年,位于河南洛阳附近。王处直墓建于年,位于河北曲阳县灵山镇西燕川村。两者时间上相差近百年,距离也相距五六百里,与山西太原北汉墓()、内蒙古“天赞二年”()阿鲁科尔沁旗的壁画墓相距更远。但三座壁画墓中出现的“叉手”礼图像和手式完全一致。 此外,我们还可从传世绘画作品中找到对应的图像信息。五代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中也出现了“叉手”礼人物图像(图10)。 图10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叉手”人物图像 研究以上文献和考古资料涉及到的时间跨度、地域跨度不难看出,在这一时期,“叉手”礼已经是完全定型化的成熟礼仪,且已广泛流行。可以充分说明,“叉手”礼在唐、五代就已经在全国、甚至边远的民族政权普遍流行,不是地域性礼仪。 三、宋代“叉手”礼动作样式最早的文字记载与图像解读 关于最早描绘“叉手”礼手形及动作具体样式的史料,可见以下两则: 南宋初年,王虚中《训蒙法》首次记载了“叉手”礼动作姿势:“小儿六岁入学,先教叉手,以左手紧把高手,其左手小指指向右手腕,右手皆直,其四指以左手大指向上。如以右手掩其胸也”。 南宋末年,陈元靓编撰《事林广记》也记载了叉手礼的动作结构要领:“凡叉手之法,以左手紧把右手拇指,其左手小指则向右手腕,右手四指皆直,以左手大指向上。如以右手掩其胸,手不可太着胸,须令稍去二三寸许,方为叉手法也。”(图11) 图11南宋陈元靓《事林广记》丁集卷上幼学类记载“叉手”礼手式要领 (采自:(宋)陈元靓:《事林广记》,中华书局影印本,年。) 通过对上述资料的分析,可得出以下三点: 第一,此时“叉手”礼已经是很流行、很成熟的常用礼仪; 第二,“叉手”礼关键动作要领是左手作掌型,右手四指皆直,左手包裹右手拇指。 第三,右手不可以太靠近胸口,至少隔着二三寸距离。 笔者认为,之所以要采取左掌包右拳的姿势,这里面包含“阴阳祸福”思想。 宋高承《事物纪原·天地生植·阴阳》说:“《春秋内事》曰:‘伏羲氏定天地,分阴阳。’” 《礼记.内则疏》解释说:“右,阴。” 《礼记·檀弓上》:“孔子与门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学也,我则有姊之丧故也。’二三子皆尚左。”郑玄注:“丧尚右,右,阴也。吉尚左,左,阳也。” 以上资料说明,从《礼记》开始的施礼习俗就是吉事尚左,凶事尚右。从后世发现的“叉手”礼史料与图像看,均采用左手成掌,右手握拳,左手包裹右手,表示的是把“阳”的一面,“吉”的一面,显示给受礼者,体现对受礼者的尊重,以达到“叉手示敬”目的。 五代十国特别是宋以后,随着卷轴画的盛行,“叉手”礼图像开始出现在绘画作品中。与此同时,在北宋、辽、金以及南宋,墓室壁画中也经常出现“叉手”礼人物图像,这两方面信息都给研究“叉手”礼带来丰富、可靠的实物材料。 南宋刘松年所作《中兴四将图卷》中,两位裨将行“叉手”礼,似乎是显示对自己主将的恭敬(图12)。 图12南宋刘松年《中兴四将图》中“叉手”人物图像 年发掘的辽宁北票季杖子辽墓中,东耳室券门左侧、西耳室券门右侧及主室甬道两壁前部分,各绘有双臂合拢,作“叉手”礼状男侍从者,左右两两相对,各与前仪卫者相接(图13)。 图13辽宁北票季杖子辽墓“叉手”人物图像 (采自:韩宝兴:《北票季杖子辽代壁画墓》, 《辽海文物学刊》年第1期。) 年6月,吉林省博物馆、哲里木盟文化局会同库伦旗文化馆对库伦旗一号辽墓(约)进行了发掘,墓道北壁墓主人出行图绘有五位汉人,装束相同,头戴交脚幞头、着窄袖中单,圆领宽袖外袍,左手握右手拇指,叉腿侍立,五人均施“叉手”礼(图14)。 图14吉林哲里木盟库伦旗一号辽墓墓道北壁出行图“叉手”礼人物图像(采自:王泽庆:《库伦旗一号辽墓壁画初探》,《文物》1年第8期。) 年7月,河南安阳县文管会发掘小南海宋代壁画墓,墓室东壁绘男仆二人,左手紧握右手大拇指,大拇指向上,二手握以胸前,作“叉手“礼,向主人致意(图15)。 图15河南安阳县小南海宋代壁画墓东壁“叉手“礼人物图像 (采自:李明德、郭艺田:《安阳小南海宋代壁画墓》,《中原文物》年第2期。) 此外,山西长子县小关村金代纪年壁画墓()墓室北壁东侧也发现了作“叉手”礼侍从像(图16)。还有辽宁朝阳市建平县黑水镇七贤营子村水泉二号辽墓(—)(图17)、辽宁朝阳市龙城区召都巴镇辽墓(—)(图18)、山东淄博市博山区神头金墓()(图19)、河南登封市王上村元墓(—)(图20)均出现了非常清晰的“叉手”礼的图像。 图16山西长子小关村金代纪年壁画墓“叉手”人物图像 (采自:长治市博物馆:《山西长子县小关村金代纪年壁画墓》,《文物》年第10期。) 图17辽宁朝阳市建平县黑水镇七贤营子村水泉二号辽墓“叉手”人物图像(采自:徐光冀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辽宁吉林黑龙江卷》,科学出版社,年1月。) 图18辽宁朝阳市龙城区召都巴镇辽墓“叉手”人物图像 (采自:徐光冀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辽宁吉林黑龙江卷》,科学出版社,年1月。) 图19山东淄博市博山区神头金墓 (采自:徐光冀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科学出版社,年1月。) 图20河南省登封市王上村元墓 (采自:徐光冀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山东卷》,科学出版社,年1月。) 年,由重庆大学人文艺术学主持的国家“十五”艺术课题“四川南宋墓葬群石刻艺术研究”中提到,泸县宋代石室墓葬中发现“叉手”礼图像(图21)、(图22),皆为男侍,头梳高髻,低眉垂目,表情恭敬,左手紧把右手拇指,左手小指则向右手手腕,右手四指皆直,以左手大指向上,如以右手掩其胸,作叉手礼状。 图21四川泸县福集镇针织厂一号墓“叉手”人物图像 (采自:李雅梅、张春新:《泸县墓葬石刻的侍者服饰》,《文艺研究》年第3期。) 图22四川泸县福集镇龙兴村二号墓“叉手”人物图像 (采自:李雅梅、张春新:《泸县墓葬石刻的侍者服饰》,《文艺研究》年第3期。) 四、唐、五代、宋、辽、金“叉手”礼图像比较与考证 关于这种左手作掌型,右手四指皆直,左手包裹右手,大拇指向上的“叉手”礼究竟何时出现,或者说何时流行,学界一直有着争议,学者大多认为最早出现在宋代。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阐述:“‘叉手示敬’是两宋制度,在所有宋墓壁画及辽、金壁画中均有明确记载。”他明确认定是:“是流行于宋元时期的手礼,非五代所有。” 还有几位学者也认为“叉手”礼最早开始于宋代。邵晓峰《韩熙载夜宴图的南宋作者考》一文将《韩熙载夜宴图》(图10)与宋《女孝经图》(图23)中“叉手”礼男子图像进行对比,也认为“叉手”礼出现在宋代而非五代,并用该类图像作为证明《韩熙载夜宴图》是宋人作品的有力证据。屈婷、冯东东《“叉手”礼新考证》一文指出:“我们查阅了众多的文献资料,其中在中国画史上的名作《韩熙载夜宴图》和《女孝经图》两幅画中发现了此‘叉手’礼的最早图形描述。” 图23宋《女孝经图》“叉手”人物图像 但笔者依据前面文献和有明确纪年的考古图像资料,认为宋人施行的“叉手”礼,在唐和五代时期就已经出现,并已经成为当时流行的常用礼仪。 如果将已发现的唐、五代、宋、辽、金“叉手”礼图像作一个系统比较(图24),可以看出,“叉手”礼从唐到南宋,从中原汉族政权到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动作基本变化不大,手式几乎一致。 图24唐—五代—宋、辽、金“叉手”人物图像对比示意图 值得注意的是,在辽宁朝阳市建平县黑水镇七贤营子村水泉一号(图25)、二号辽墓(—)(图26)、河北宣化下八里辽代张匡正墓()(图27)、内蒙古库伦旗奈林稿公社前勿力布格村6号墓(—)(图28)、陕西甘泉县柳河湾村金墓()(图29)中出现的“叉手”礼人物图像,与陈元靓编撰《事林广记》记载的叉手礼动作结构略有区别,均系右手紧把左手拇指,至于出现此类图像的原因,是因画工在绘制壁画时粉本运用的失误,还是当时就已经并存有右手紧把左手拇指的叉手形式,还有待结合文献作进一步考证。 图25辽宁朝阳市建平县黑水镇七贤营子村水泉一号辽墓“叉手”人物图像(采自:徐光冀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辽宁吉林黑龙江卷》,科学出版社,年1月。) 图26辽宁朝阳市建平县黑水镇七贤营子村水泉二号辽墓“叉手”人物图像(采自:徐光冀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辽宁吉林黑龙江卷》,科学出版社,年1月。) 图27河北宣化下八里10号张匡正墓“叉手”人物图像 (采自:徐光冀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河北卷》, 科学出版社,年1月。) 图28内蒙古库伦旗奈林稿公社前勿力布格村6号墓“叉手”人物图像 (采自:徐光冀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内蒙古卷》, 科学出版社,年1月。) 图29陕西甘泉县柳河湾村金墓“叉手”人物图像 (采自:徐光冀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陕西卷》,科学出版社,年1月。) 五、结语 从“叉手”礼发展的源流看,作为佛教礼仪之外的世俗礼仪一种,于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分流行。但在唐代之前,因资料和图像的缺失,已经无法知道这种礼仪的具体动作。从现已获知的唐、五代及宋代史料和图像看,“叉手”礼这种独特的礼仪,在唐、五代已经是当时很成熟的常用礼仪了,而并不是到宋代才出现与流行。 关于“叉手”礼的功能,根据图像生成的环境和场景不同,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种: 第一、仅作为世俗交往的一种礼节,没有体现尊卑关系功能; 第二、属于从宗族制度、贵贱等级关系中衍生而来的尊卑之礼,主要体现上级与下级、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层级关系。 此外,从“叉手”礼出现的时间及流行区域来看,可以认为,此礼早期为汉族常用的礼仪,南、北地区均流行。之后逐渐流传至边远的民族政权和少数民族地区。 本文只是尝试对“叉手”礼图像作了初步的研究,目的在于提出这一现象,许多细节性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展开,某些观点与结论还是暂时的,随着考古新资料的不断发现与更多学者的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nhukb.com/wqbbzl/4996.html
- 上一篇文章: 薛之谦晒娃遭打脸,新生儿的握拳能不能强行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